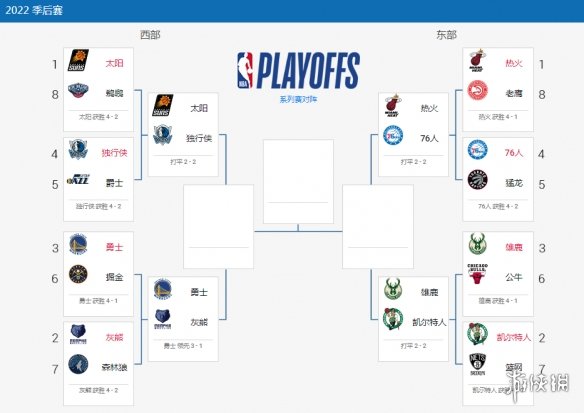
■马艳
面对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Felix Gonzalez-Torres)作品的最初场景,是在举办已近十年的《美国艺术三百年——适应与革新》之际,那是一大堆呈现出极简形状的美国糖果,参观者惊异于这件现成品可以被随时取食,而其本身正在逐渐消失。这件名为《“无题”(舆论)》的作品就像早已离世的艺术家,其相关影响力犹如“深文隐蔚,余味曲包”而能在二十年之后的上海外滩美术馆为其所举办的一场回顾性展览中呈现出来。
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在当代艺术史上曾具有广泛影响力,被法国理论家尼古拉斯·伯瑞奥德确认为“关系美学”理论的早期代表性艺术家,而显然时值这位美国传奇艺术家逝世二十周年之际,以“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为名的中国首场个人大型展览显得有点姗姗来迟,但似乎又颇具纪念之意义。此番展览被上海外滩美术馆认为是“艺术家以突破传统的创作方法以及作品中尖锐的敏感性而享有广泛的声誉,其作品的特性也使得本次展览超越了一般回顾展的范畴,更包含了对其艺术的创新性解读和全新构建”之意义。
而从展览现场所呈现的从全球三十家艺术机构甄选的创作于一九八七至一九九五年间的四十余件作品来看,虽然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对于生活物品采用了较为国际化的极简形式来加以轻巧的归纳和挪用,未施以刻意人为的痕迹,从而使得作品整体展现出艺术语言较为弱化的观感,而所谓“关系美学”的相关理念,如“这类作品声称不再制作物体、意象或者信息的复制品,而是致力于真的行动或真的物品,从而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形式和环境”则在这些作品的物质表面浮现出来。但艺术家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并没有以此滑入概念艺术的枯燥之中,而是以其惯用的糖果、灯泡、窗帘,纸堆,镜子、珠帘等日常材料,以圆形、对偶、序列来形成一种新的艺术关系的结构与生成。
圆形与对偶
在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的九十年代作品中,圆形和对偶的形态关系成为其主要线索之一。最初在创作于一九八七年的贴纸转印作品《双重恐惧》呈现了在黑白色底上间接变幻的圆形图谱;而一九八七至一九九0年间,由两个壁钟对称构成的《“无题”(完美爱人)》则开始加入了对偶的作品关系,包括此后在一九九一年创作的名为《“无题”(双重肖像)》的无限量纸上印刷品,以及由两片圆形镜子对称组成的《“无题”(3月5日)#1》都以优美而简约的金色圆弧和圆形镜像来延续了圆形和对偶的线索。而在作品《“无题”(俄耳甫斯,两次)》中,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把对偶的关系放到变体的形状之中:两扇略高于人体的长条镜子以此并列呈现,展厅和观者以此对照出自身和环境的某种镜像。
序列
而在以圆形和对偶关系展开的实践之下,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逐渐展开了更广泛的类型化创作,逐渐形成一种挪用序列化的现成品而形成极简主义美学而闻名的创作模式。从一九九一年的《“无题”(摇摆舞台)》到同样创作于一九九三的《“无题”(北)》、《“无题”(余晖)》和《“无题”(舞场)》,艺术家都以灯泡的日常属性来串连形成发光的现场,例如《“无题”(摇摆舞台)》便是以摇摆舞者穿着银丝短裤、运动鞋,携带个人音乐设备,来进行一场随时展开的领舞演出,而参观者们也成为展厅舞场的一份子。《“无题”(北)》则贯穿于美术馆二楼到五楼的楼梯井中,用点点灯光照亮了每一步阶梯。观众也可以在《 “无题”(舞场)》恍惚的光影中与自己的同伴一起戴上耳机,随着音乐跳一支华尔兹。
彩色糖果作为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又一标志性的作品材料,在一九九一年分别创作了《“无题”(罗斯在洛杉矶的肖像)》和《“无题”(舆论)》,尤其前者为冈萨雷斯-托雷斯最为人所知的作品之一——以黑色杆状甘草糖形成无限量的尺寸可变的糖果集群,这是一件极为敏感和微妙的肖像:无需再用照片或者绘画来描绘这个无比熟悉的人的脸孔和外表,只需要一个亲密的、诗意的、情欲的动作,把一个人的身体与另一个人的身体相连。糖果的重量随着时间而逐渐消减,一如罗斯病重时逐渐消瘦直至最终失逝去的情景。而后者则配以彩色迷人的玻璃包装纸,这件作品也借助观众的取走、品尝,来体味甜蜜之后逐渐消失的经验体会。
而珠帘和窗帘所隐含的暧昧与隔绝之属性在一九九一年的串珠和悬挂装置《“无题”(化疗)》和创作于一九九五年的《“无题”(金)》表达出类似的经验,而在一九八九年《“无题”(情郎)》作品,则是以蓝色织品形成随风而浮动的窗帘装置,摇曳于二楼窗边的淡蓝色纱帘为美术馆的空间蒙上了一层浪漫温柔的滤镜,但这颇具诗意的作品需要午后的阳光和清风,显然这是在中国现场难以实现的作品必要元素。
而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更大量的作品面貌是以印刷品来实现。一九八八年的《“无题”》就是以装裱影印照片和彩色照片拼图来构成,而一九九0年的《“无题”(终)》则以数量无限的纸上彩色印刷来堆叠成一种极简的几个形状,包括同为蓝色的一九九0年《“无题”(情郎)》,以及一九九一年厄《“无题”(我们不记得)》,这些印刷品堆积成理想高度,留待观众来取阅并带走,以此完成作品概念的传播和实现。
关系
对于一位往往以身边日常的物件为材料的艺术家来说,众多作品展览中的灯泡、挂钟、糖果、镜子,甚至一串日期都既是作品本身,也是解读作品的线索。冈萨雷斯-托雷斯以此邀请观众通过视觉、触觉,乃至味觉的多重体验,来体验公共与私人,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张力、融合与对抗,以此构成了其艺术创作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而现场所展出作品的稀疏布置也提醒着观众对其作品的物质属性的敏感度:它们对存在和缺席、对顺应力和脆弱的暗示,思考了稳定与流动之间、邻近和远距离之间、统一与混乱之间、和谐与不和谐之间的永恒不定的结构关系。
在公众号页面
点击点我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